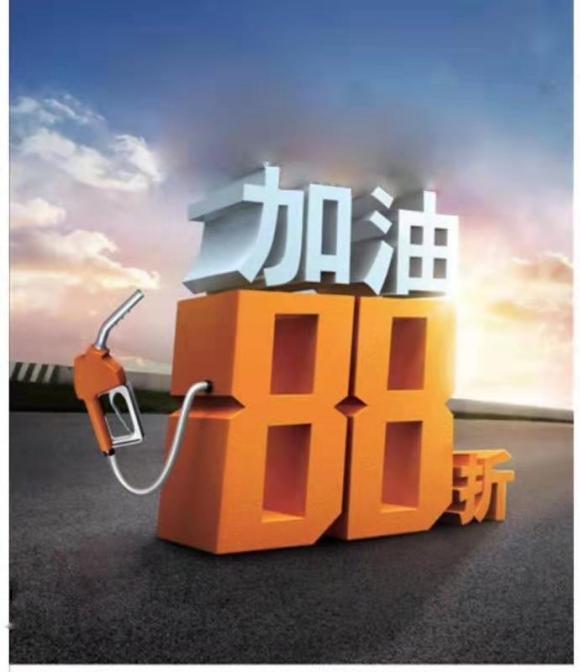老年人應當活得輕松自如
時間:2024-10-17 來源: 作者: 我要糾錯
新的世紀,我們將步入老年社會,老年人的命運必將與國家、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。”這是從宏觀的角度而言。即使從個人的角度出發,這一話題也具有深刻的意義。
從新生走向衰老,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命規律,老年人的今天,便是中年人的明天、青年人的后天,因此,討論老年人的生活,作用并不局限于老年人,對全社會各個年齡層次的人群都具有指導的意義。朋友離退休前的職務不同,文化程度不一樣,所從事的工作也有,離、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更是干差萬別。然而,心愿只有一個:要使晚年過得更有意思。盡管各有各的話法,也還是有許多共同的地方,對生活有不少一致的看法。
要活得輕松、充實、有價值,首先不要活得太刻意。我們所說的老年人,都是離開工作崗位的人,是生活上最自由的一族。不必為案牘而勞形,不必為人事而費心,最大的優勢就是自由自在地生活。對老年人的生活決不應該提出什么“指導性”的意見。親自參加“四化”,奉獻余熱固然很有意義,但幫助兒孫做點家務,減輕他們的壓力,讓她們更加專心致志地工作,也是對社會的貢獻。身強體鍵,親力親為,固然會受到社會的歡迎,但善自保養,自愛自珍,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報。至于生活規律,譬如作息時間、起居節奏、飲食習慣等等,更不必強求一致,怎樣過得最舒服就怎樣過,在這里可以借用一句流行歌曲里的話:“跟著感覺走”。要活得輕松自如,必須增加生活的情趣。
老年人的活動,目的在于拾情養性,延后益壽,做起來必須感到有趣味。平時參加些什么活動最有意義呢:完全視各自的情況而定。有些同志是部隊的熔爐煉出來的,大半輩子戎馬倥傯。離、退休后想生活得“文”一點,習點詩文,學點繪畫;有些同志一參加工作便埋頭案牘,文山會海,今日得寬余,便想增加生活中“武”的成份,打打拳,舞舞劍。不論是學詩繪畫,還是打拳舞劍,都不必像私塾的學童和武館的學徒那樣刻苦,那樣賣勁。假如“為伊消得人憔悴”,那便事與愿違了。
但我們不贊成面對往日的許多遺憾采取無可奈何的“算了”的態度,而是主張采取積極的“補償”方式。如何“補償”呢:有些老同志顯淺地總結為“缺啥補啥”。有一位離休老干部告訴我,過去工作繁忙,很少與子女共敘天倫。離休了,要補一補,他買了一輛小三輪車,每天騎車送孫子、孫女上幼兒園,又把他們接回家,假日還用車子載著兩個小家伙滿城轉,優哉悠哉,好不滿足。另一位老同志離開基層時間較長,回憶起當年老同事對自己的支持和幫助,總覺得欠著一筆人情債,退休后,他便堅持每年“探家”一趟,回老單位找當年的伙伴聊天,歡聚數日,每次歸來心胸都倍覺充實。我們這樣說,并不是提倡“隨心所欲”、“為所欲為”。
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,總要受到社會的制約,生活是有邊有際的,這個邊際就是道德與法律。老同志要保持晚節,晚節不保便談不上價值了(我們建議對此開展一次專門討論)。在保持晚節的前提下,生活得越隨意越好。
從新生走向衰老,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生命規律,老年人的今天,便是中年人的明天、青年人的后天,因此,討論老年人的生活,作用并不局限于老年人,對全社會各個年齡層次的人群都具有指導的意義。朋友離退休前的職務不同,文化程度不一樣,所從事的工作也有,離、退休后的生活方式更是干差萬別。然而,心愿只有一個:要使晚年過得更有意思。盡管各有各的話法,也還是有許多共同的地方,對生活有不少一致的看法。
要活得輕松、充實、有價值,首先不要活得太刻意。我們所說的老年人,都是離開工作崗位的人,是生活上最自由的一族。不必為案牘而勞形,不必為人事而費心,最大的優勢就是自由自在地生活。對老年人的生活決不應該提出什么“指導性”的意見。親自參加“四化”,奉獻余熱固然很有意義,但幫助兒孫做點家務,減輕他們的壓力,讓她們更加專心致志地工作,也是對社會的貢獻。身強體鍵,親力親為,固然會受到社會的歡迎,但善自保養,自愛自珍,也是對社會的一種回報。至于生活規律,譬如作息時間、起居節奏、飲食習慣等等,更不必強求一致,怎樣過得最舒服就怎樣過,在這里可以借用一句流行歌曲里的話:“跟著感覺走”。要活得輕松自如,必須增加生活的情趣。
老年人的活動,目的在于拾情養性,延后益壽,做起來必須感到有趣味。平時參加些什么活動最有意義呢:完全視各自的情況而定。有些同志是部隊的熔爐煉出來的,大半輩子戎馬倥傯。離、退休后想生活得“文”一點,習點詩文,學點繪畫;有些同志一參加工作便埋頭案牘,文山會海,今日得寬余,便想增加生活中“武”的成份,打打拳,舞舞劍。不論是學詩繪畫,還是打拳舞劍,都不必像私塾的學童和武館的學徒那樣刻苦,那樣賣勁。假如“為伊消得人憔悴”,那便事與愿違了。
但我們不贊成面對往日的許多遺憾采取無可奈何的“算了”的態度,而是主張采取積極的“補償”方式。如何“補償”呢:有些老同志顯淺地總結為“缺啥補啥”。有一位離休老干部告訴我,過去工作繁忙,很少與子女共敘天倫。離休了,要補一補,他買了一輛小三輪車,每天騎車送孫子、孫女上幼兒園,又把他們接回家,假日還用車子載著兩個小家伙滿城轉,優哉悠哉,好不滿足。另一位老同志離開基層時間較長,回憶起當年老同事對自己的支持和幫助,總覺得欠著一筆人情債,退休后,他便堅持每年“探家”一趟,回老單位找當年的伙伴聊天,歡聚數日,每次歸來心胸都倍覺充實。我們這樣說,并不是提倡“隨心所欲”、“為所欲為”。
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中,總要受到社會的制約,生活是有邊有際的,這個邊際就是道德與法律。老同志要保持晚節,晚節不保便談不上價值了(我們建議對此開展一次專門討論)。在保持晚節的前提下,生活得越隨意越好。
標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