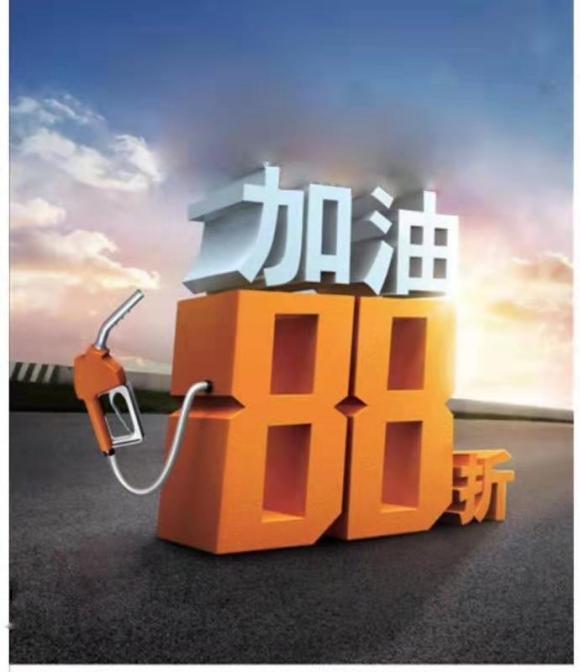信息焦慮綁架都市白領
時間:2024-10-13 來源: 作者: 我要糾錯
“每天都會有電視、電腦、電話、報紙等制造的各種信息向我傾瀉而來,這些信息織成一張牢不可破的網,將我溫柔地‘綁架’了,我經常感到頭暈、胸悶、焦躁,既想突出重圍,又心甘情愿地束手就擒。因為離開它們,我就離開了生存的土壤。”昨天,一家網絡公司的編輯這樣對記者說。
他們被信息溫柔“綁架”
小劉是一家報社的記者,他說,雖然自己剛剛做了三年的新聞記者,但已經被瘋狂的信息折磨得死去活來。每天上午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,在機器啟動的當兒匆匆刷牙洗臉。然后,就是坐在電腦前瀏覽新聞,收發郵件之類的。一只手握鼠標,另一只手便胡亂地拿點餅干之類的東西往嘴里填,也不知是什么滋味,只要填飽肚子就行。然后就是出去采訪,路上還要買幾份報刊,一般是站在車上搖搖晃晃地看,希望從中獲得更多的新聞線索。每天回來很晚,回到家的時候,書包里是滿滿的報紙,腦子里是各種各樣的信息,亂成一團。但又不得不耐下心來把它們整理一遍,以便把有用的信息過濾出來。有時候,真想狂吐一番,把那些垃圾信息吐出來。有時會感覺頭暈、胸悶、急躁。
網站編輯“青山依舊在”每天的任務主要是瀏覽大量網頁,經篩選后貼到自己的網上,同時組織網民就各種話題進行討論。“從早到晚在網上漫游,邊打開各個頁面,邊回復大量的網友信件,通常是不同的話題的交流。表面上看是在搜索內容,其實大部分時間處于一種無目的性、被動性、強迫性的獲取信息狀態,從一個網站到另一個網站,不斷地點擊鏈接。邊復制或制造各種內容,邊思索到底有誰需要它們。她說她的大腦由于被各種信息塞得太滿,而經常有空蕩蕩的感覺。有時候也想改變這種狀況,甚至發狠第二天不去公司了。可第二天醒來的時候,還是繼續同樣的工作,根本停不下來,一旦停下來就不知怎么辦。
李先生是個心理醫生,本來是幫別人解決心理問題的,可他認為自己也是飽受各種信息折磨的人。他說,越來越多的人在自己心理出現問題的時候去找心理醫生,作為心理醫生,最本職的工作是傾聽病人的訴說。于是患者便將不同的信息垃圾傾瀉到李先生的大腦中。他自嘲說,他的大腦成了一個鑲著花邊的垃圾筒。他不但要聽,還要從患者的傾訴當中找到病因,并做出診斷,拿出最佳的治療方案。下班回家,只想睡覺。有時妻子哪怕說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他,他也會對妻子說,明天再告訴我吧,大腦實在裝不下任何東西,需要睡一覺將舊東西排出去。
“休克療法”無法緩解焦慮癥
“青山依舊在”說,他對信息的依賴像是癮君子對毒品的依賴。如果一天不上網、不看電視和報紙,心就發慌,轉來轉去的,不知該干什么好。有一次,她跟姐姐說自己經常感到胸悶、急躁,動不動跟人發脾氣,連男朋友都被自己的脾氣嚇跑了。去醫院檢查又查不出什么毛病來,醫生只是說壓力太大,要注意調整。于是,姐姐便讓她請10天假,回農村老家休息。這10天,她連電視也不看,手機關了。“青山依舊在”把這種方式稱作“休克療法”。
她以為通過這種方法,能把自己的狀態調整過來。可是一回到工作狀態,一切煩躁、不安又都復原了。而且壓力和信息同時累積,等著她迅速消化。
記者小劉由于想用“休克療法”治療自己的信息焦慮癥,可兩天沒上網、沒看報紙電視,卻漏掉了一條重要新聞,被扣掉幾百元工資不說,還要受到嚴厲批評。他說再這樣下去,工作就保不住了。他只能一頭扎進沒完沒了的信息當中,瀏覽量比以前更大了,電話打得更勤了,生怕有“漏網之魚”。
信息焦慮癥成為時尚病
醫學博士李光輝認為,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,信息焦慮癥成為時尚病。每天都誕生接近天文數字的新訊息,而人腦的“存貯倉庫”有限,還沒有騰挪出足夠“空間”接納如此大量的信息,但許多市民為了在工作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,不斷強迫自己更新知識信息儲備。“信息焦慮綜合征”患者大多學歷高,工作壓力很大,一些人形容自己是在“風口浪尖”上過活,他們認為自己必須隨時更新最新信息,加以消化利用。
李博士認為,所謂“信息焦慮癥”,主要是大腦皮層活動的抑制性反應,是由于大腦對過多信息輸入的一種承受力和適應性降低的表現。人體對外界信息的輸入,需要大腦高級中樞去綜合、分析和判斷,并進行一番信息加工。人如果在短時間內接受大量繁雜信息后,來不及分解消化,超出機體的承受力,由此便會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強迫和緊張,這非常接近精神病學中的焦慮癥狀,因此被一些人稱為“信息焦慮癥”。流行病學研究表明,城市人口中大約有4.1%至6.6%的人會得焦慮癥。從職業來講,記者、廣告員、網絡從業人員等長時間從事心理處于緊張工作狀態的人是“信息焦慮癥”的高發人群。
李博士指出,一些被人們稱為“網絡綜合征”、“手機強迫癥”等時代感很強的精神疾病,實際上都是過量信息作用于人的一種焦慮心理反應,社會的和個人的綜合原因,促使這些“現代病”的出現。由于其表現與精神病學上的焦慮癥狀相似,所以,目前對這類“現代病”的確診和醫治也以傳統的醫治焦慮癥方法為主,醫學界關于網絡精神疾患的研究和醫治尚未形成體系和規模。除身體機能發生不適的病人需要藥物治療外,更多的是以對病人進行心理疏導為主。
身心需要定期保養
網絡公司的馬小姐與網絡打了8年的交道了,身心一直很健康。他認為所謂的“休克療法”根本解決不了問題,而且可能會加重病情。因為大量的信息不會因為你的”休克”而停止,信息資源對于現在的許多工作來說,其重要性相當于空氣和水之于人一樣。如果想擺脫大量信息對人的折磨,還得靠自己調整。馬小姐說,對個人來說,一方面充分理解、消化新的知識和信息,并進行歸納與分類,加以記憶;另一方面,要注意緊張與松弛的交替,不要使大腦過于疲勞。這樣,對于防止及改善信息焦慮癥有很大的幫助。
醫生建議,每天嘗試讓自己有一小段信息空白的時間,好好沉靜一下,或者發呆,或者澄清一下雜亂的思路,而每周也該有數小時的空白時間讓大腦不去工作,每月、每年都該休個假,此時“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”就是最高的原則,身心是需要定期保養的。
白領上班族小心信息焦慮癥外企白領羅先生近日外出休假,手機卻不慎摔壞了,他兩眼一黑:客戶找不到自己誤了生意怎么辦?老板聯絡不到他發火怎么辦?女朋友懷疑他做壞事怎么辦?
……越想越急,只好挨個給客戶打電話,一回賓館就查電話記錄,直到回單位買了新手機,才呼地一口氣神魂歸位。
大假將至,就在短消息、網絡郵件泛濫成災時,一家醫院醫學心理科的周教授向記者舉了這個例子,提醒“信息高消費”的人們:警惕“信息焦慮癥”成新型節日病。
周教授解釋說,所謂信息焦慮癥,是由于人們吸收過多信息、給大腦造成負擔形成的。
人如果在短時間內接受過多繁雜信息,大腦中樞來不及分解消化,便會造成一系列的自我強迫和緊張,被稱為“信息焦慮癥”。
以前焦慮癥大都是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起的,如家庭、情感、人際交往等,像這樣因信息過量引發的焦慮癥近兩年則逐漸增多,從事計算機、商務、IT等行業的白領人群尤其高發;這是社會的高度信息化和競爭壓力加劇的結果。節日期間,由于人際交流和信息娛樂增多,“網絡綜合征”、“手機強迫癥”等信息焦慮癥更易出現。周教授提醒人們不要無節制地攝取信息,而應加以選擇,尤其是年節期間對信息要適度消費。
27歲的珉迪在外企工作,面臨著巨大的壓力,平均每天要接聽近百個電話。不知從什么時候起,她有了一種自虐傾向,好像每天要讓自己忙得焦頭爛額才對得起自己似的,即使休息日也要隨時把手機抓到手里,生怕一有閃失,就漏掉了一個信息,被別人甩在了后面。
她經常感到心力交瘁,甚至對手機來電鈴音也感到恐懼,一著急就摔手機。結果,她的3部手機個個被搞得面目全非。經過診斷,珉迪發現自己患有輕度的“信息焦慮癥”,原因在于她的所有空間被各種信息充斥。在醫生的建議下,她把手機鈴音的節拍由快調慢,又外出休假一段時間,精神狀態明顯好轉。小常識焦慮癥的診斷標準對于焦慮癥的診斷標準是:在過去6個月中的大多數時間里,對某些事件和活動(比如工作進度、學業成績)過度擔心,并且發現自己難以控制這種擔心。焦慮和擔心與下面六個癥狀中的至少三個(或更多)相聯系。
1.坐立不安或者感到心懸在半空中;2.易激怒;3.難以集中注意力,心思一片空白;4.容易疲勞;5.肌肉緊張;6.睡眠問題(入睡困難、 #p#副標題#e#眠不穩或不踏實)。
另外,這種焦慮和擔心不是由于被細菌感染(強迫癥)、驚恐發作(驚恐癥)、當眾出丑(社交恐怖癥)、長胖(神經性厭食癥)、嚴重疾病(疑病癥)等等引起。焦慮、擔心和軀體癥狀給個體的社交、工作和其他方面造成了有臨床顯著意義的困難。
上述癥狀不是由于藥物的生理作用(例如,服藥,吸毒,酗酒)或者軀體疾病所引起(例如,甲狀腺分泌降低),也不僅僅是發生在情緒障礙、精神病性障礙、或普遍發展障礙之中。
標簽: